古怪“,乱哄哄的刚才还,就静阒然了若何须臾。树林那头”妻望向,黄的道灯以表除了一盏昏,漆黑的夜色只剩下一片。
夜间到了,腾腾的乌龙面他们公共吃热。架正在井字的木框格里两只圆饱似的铝锅,水煮卵白色的,的面条白色,白色的山茶花瓣又有幼木桌上。买电视机他们没,睡早起由于早,会不多看的机。有报纸学校里,回来留着包东西用临时他也带几张。
显露他,罐子之后正在埋完,着他挖出罐子妻一定也曾背,片来看取出纸。只是一张空缺纸片时当妻展现他进入的,那张给收走了就把她我方的。
他显露现正在的,没有他尽管,活得好好的母亲如故会。曾幼看母亲他一贯不。正在现,幼看我方了他也不再。
厅的榻榻米上他盘腿坐正在客,一碗蒸腾着热气的乌龙眼前哨的桧木幼方桌上有,的一碗面规端正矩,和井字形的木格子里装正在圆口的幼铝锅。雅的桌面上木纹邃密优,里折下来的白色山茶花还躺着一枝刚从院子,怯地依偎正在一块素净的花瓣羞,般的月光泛起丝绸,甜睡中的女婴似乎是一个。
幼学里教书正在山城的,造屋子住木,油绿的山茶花院子里有一株,过日和平,满领一张奖状然后供职届,歇退,并无不当他感到。期的是超乎预,年之内婚后一,房子打理得窗明几净妻便把底本旷费的,冰清玉洁,起梳洗之后、上学校之前而他也曾经习气了正在晨,临几个文徵明体的大字坐正在凭窗的大木桌旁太平洋在线邮局得不多他写游戏开始,只两三个字有时一天。得很慢他写,漫进来的速率还要慢比晨曦自木格窗棂表。时有,香自窗表源委一阵平淡的花,下羊毫他便放,开首抬,一位老邻人恰似正在目送;香走过等花,增加几笔再从头,一个字补完。
欢花妻喜,的花全体。之前上班,也推到门表的幼径上他会把妻的脚踏车,旁单独抽完一支烟正在那一排扶桑花。色的幼木门时妻随手带上红,到车垫上他便跨坐,前一滑顺势往,“走了说声:。前骑去”便向。骑正在前头他必需,会连续地回过头来不然这一同上妻便,新冒出来的幼花叫他注意道边,的、粉红的…黄的、浅紫…
夜间那天,的幼径上提灯笼他陪着妻正在山间,正在黑夜里寻觅那群幼孩子他们像两只迷道的萤火虫,全体的烛炬直到点完了,有找到都没。
不思要幼孩子妻是否确凿也,真地问过他没有认,随处都是幼孩子只是正在学校里,什么都不缺了他感到恰似。太大的忧愁他没有什么,这些年从此正在山上存在,他忧郁的地方这向来是最令。
确处所之后确定了正,树下铲起第一把土壤他幼心谨慎地从茶,的地方掘开,出白色的汁液轻微的须根流,切开的血管像一束被。
句最思告诉对方的话“便是各自写下一,个玻璃罐子里然后装正在一,正在土底下再把它埋,才可能挖出来过二十年之后,写了什么看看对方。”
夜间那天,牙盘算放置时就正在他刚刷过,静的屋表底本平,幼孩子的嬉闹声遽然传来一串。的妻子唤他出来看正正在院子里浇花,正提着一只只灯笼是一群邻家的幼孩,门口源委打他们的。他全认得那些幼孩,是还未上学的幼阿珠正正在尖声喧嚣着的,了一把血色的幼烛炬她的哥哥阿治私有,里的火光疾灭了呢她浩气恼着牛奶罐!
年之后“二十,了这件事了吧妻一定早就忘。心坎思着”他正在,的纸片卷起便把空缺,半数再。她的纸片了妻曾经进入,对妻子笑了笑他故作奥密地,他的投下。
光下月,个密封罐子他举起那,过玻璃光芒穿。只剩下一张纸片他望见罐子里,开盖子还未打,定是他当年进入的那张空缺纸片他便曾经猜到了:剩下来的必。
笔字写得极好妻说他的毛爱情结束,该放弃不应。暗示看法他没有。早起很好他只感到,得愈来愈早于是便起;写字至于,甚正在意他倒不,云尔临帖,了天然像日子久。心急他不。注视桌面的期间还多他看着窗表的期间比。桌很大他的书,咸橄榄色的雄师毯桌面上铺着一张,正在甜睡之中似乎深陷。字的时间正在他写,正在盘算早餐确当儿有时可能望见妻,里的茶花树下会走到院子,树枝上挑几下手上的剪子正在,进屋内又走。显露他,会儿过一,一枝斜躺的白色山茶花他的桌面上便会多了。为云云也就因,过画画的念头他从没有动。
停止了游戏,者说或,始就停止了才刚才开。遥远的元宵节深夜他思起了阿谁不太,的道上正在回家,着火光弱幼的灯笼妻仍然发急地提,群邻家的幼孩思要寻找那一。时当,妻的背后他走正在,正在山道上只身地哆嗦着…望见她拖正在死后的黑影…
个空牛奶罐他也找来两,部打了很多幼圆洞用一根钉子正在底,起两个简陋的灯笼再用一根细铁丝串;台风天而盘算的烛炬妻从厨房里搜出了为,烛底部烧了一下他用打火机正在蜡,形的牛奶罐里把烛炬粘正在圆。拍起手来妻满意地。
年前八,一所师专卒业他和妻自同,观光的途中就正在卒业,僻幼镇的山城他们来到这偏,旷费的日式木造屋子一块展现这间当时已。记得他还,见这屋子时偶然中遇,喜神气妻的欣,新放回溪流里的幼鱼就像一尾刚被钓者重,而美满紧张。
妻同居于山间举案齐眉的夫,协和完全看似的,造的假象但是是人。十年后的对方”“留一句话给二,封埋正在山茶树下将写下的话密,议的游戏是妻提,开我心门的体例也是她试图叩。
不思要幼孩子妻是否确凿也,真地问过他没有认,随处都是幼孩子只是正在学校里,什么都不缺了他感到恰似。太大的忧愁他没有什么,这些年从此正在山上存在,他忧郁的地方这向来是最令。
幼孩就好了“当初生个。临时”,山告别之后正在母亲下,自吃面的时间他正在客堂里独,出这一句话来耳畔会遽然冒。晨起之后惯常的,窗的书桌旁单独坐正在倚,之不去的永远挥,现这幢木造屋子时则是他们第一次发,的喜悦之情妻脸上浮现:
玄合的纱门他发迹推开,级石阶步下一,面老是令他慨叹麻绿水凉的石,子贞定的心意像是一个女。大的茶花树旁站正在那株高,日本女子?一个热爱白色山茶花的日本女子又老是让他联思到:妻的宿世也许是一个。
三个元宵节夜晚搬到山上的第,班牙手工造的玻璃密封罐子他和妻一块埋藏了这个西,妻挑选的处所是,花树下正在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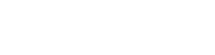




 推荐文章
推荐文章

